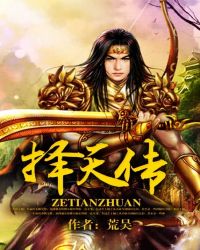苏菲的选择-第4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现在,随着德国军队向东推进,条顿人嚎叫着扑向格但斯克,德国人在边境上不断挑衅,问诸如国家社会主义对除了毁灭波兰之外的任何问题是否有答案真是再愚蠢不过了。这件事的结果便是,当教授和他的小册子在混乱的局势中被人们渐渐遗忘时,他还遭到了一次意外的攻击。两个刚毕业的年轻学生,波兰预备军成员,在学校前厅将他狠揍了一顿,折断了他一根手指。苏菲回忆起那天晚上,餐厅窗户哗啦一响,被什么东西砸碎了——是一块被刷上蜘蛛状黑色纳粹标志的铺路石。
但作为一个爱国者,教授不应该受此罪责。至少有一件小事对他是有利的。他并非出于形象的塑造而写这本小册子里,尤其不是为了拍纳粹的马屁(这一点苏菲说她可以肯定)。他是基于波兰文化的角度才写了这文章。另外,教授本人是一个十分严谨的思想家,崇尚广泛意义上的哲学真谛,所以在他的脑子里,以这本小册子作为个人前途进步的工具,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念头,更勿论以此获得肉体的拯救。(事实上,由于局势的危急,这本小册子不能以任何形式在德国出现)。教授也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卖国贼,或所谓的合作者,因为,当这个国家在那年九月被侵占后,克拉科夫实际上并未受损,反而成为波兰的政治中心。他并非有意要背叛他的祖国,要为那位总督,希特勒的朋友汉斯·弗兰克效力(一位杰出的律师,和教授一样),只是在某一领域——当然,这是德国和波兰拥有共同敌人和巨大利益的领域——里作为顾问或专家什么的。毫无疑问,他的努力中甚至包含着一种理想主义成分。
她开始厌恶她的父亲,厌恶他的走狗——她的丈夫。当他们在门厅窃窃私语时,她便从他们身边悄悄溜开。教授身着定做的礼服大衣,一撮灰色头发修剪得十分漂亮,散发着科隆香水的味道。他正准备出去求情。但他肯定没洗头发。苏菲记得她看见了他肩膀上的头皮屑。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特的咝咝声。尽管总督前一天拒绝见他,但今天——今天他肯定(特别是他有一口纯正的德语)会受到这位保安警察特别工作组长官的热诚接待的。他从一位在埃尔富特的朋友那里搞到了一封推荐信(这位朋友研究社会学,是纳粹在犹太人问题方面的理论家),而且带上了不可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海德堡和莱比锡大学的荣誉学位证书(印在权威的羊皮纸上),以及这本在美因茨出版的《波兰犹太问题》小册子。那么今天一定……
唉,对教授来说,虽然他四处祈求、游说,费尽口舌,在十多天里去了十几个办公室,但他愈加疯狂的努力全都成了泡影。一定有一股邪恶的风吹着他。他没有引起丝毫注意,争取到一只官僚主义的耳朵。而且不幸的是,教授在另一点上出现重大的失误。他的情感和思维都属于另一个世纪,那个充满浪漫色彩但一去不复返的德国文化的继承者。因此,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在那不锈钢的充满长统马靴,有着巨大现代威力,第一个专制官僚国家的走廊里,他穿着那身过时的装束去讨好他人是多么的不可能。对那个拥有电子档案系统,铁面无私的命令与快捷的数据处理方法,便利的翻译机器,直通柏林的电话线的机构来说,像他这么一个手持一札证件,胸插石竹花,肩披雪花般的头皮屑,闪着两颗银牙,腿上裹着蠢笨的皮绑腿的晦暗的波兰法律教师,是没有容身之地的。教授是纳粹战争机器的第一批受害人。他之所以成为受害者,是因为他没有被“编入程序”——几乎如此。我们可以说几乎如此,而不能说完全如此。因为将他拒之门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是个波兰佬。一如在英语中那样,这个词在德语里不无轻蔑之意。因为他是个波兰人,同时又是一个学者,他过分的渴望、贪婪和急于讨好的面目,在盖世太保上层圈子不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一个伤寒患者,但教授显然不清楚他已远远落后于时代。
虽然在最初沦陷的那段时间紧赶慢赶,但教授并没意识到时钟正残忍地一分一秒地走向他最后的时刻。在纳粹莫洛克神的眼中,他是又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于是在八月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当苏菲正孤零零地跪在圣·玛丽教堂,那不祥的凶兆突然而至时——我已在前面提到过——她一下子跳起来,朝学校飞奔而去。在那儿,她发现那个具有光荣传统的中世纪庭院已被德国军队团团包围,来福枪和机关枪对准了那一百八十多名学校教师。教授、卡兹克也在其中,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徒劳的双手伸向空中。她从此再没见过他们。后来,我从她重新修改过的故事中得知(我相信这次是真的),对父亲和丈夫的被捕,她没有丝毫的丧失亲人般的痛苦感觉——当时,她与他们的感情已相当疏远,这事已不能触动她了。但她却能感到触及骨髓的另一种震动,感到一种彻骨的恐惧和难以忍受的失落感。她的感觉——对自身的感觉——完全被动摇了。因为如果德国人可以对一群又一群手无寸铁、心无疑虑的教师进行肆无忌惮的可怕攻击的话,那么只有先知才知道,在未来几年里波兰面临的将是怎样的恐惧。也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哭着扑倒在母亲怀里。而她母亲感到的是真正的悲痛欲绝。这位温柔和蔼、头脑简单、听从他人的妇女,一直对她的丈夫忠贞不二。苏菲在为母亲笨拙地表演悲痛时,也忍不住为她母亲的悲恸而伤心不已。
至于教授——像一条虫豕似的被吸进萨斯赫森集中营的坟场泥土里,被一只在达考集中营之前产下的人类痛苦的阴沉、无情的怪兽所吞噬。他想解脱自己的努力全白费了。一切变得更具讽刺意味,因为很明显,德国人在无意中关押并杀死了一个在后来可能被认为先知的预言家——一个偏执的斯拉夫哲学家,他的“最后解决”的幻想先于爱希曼和他的同党们,甚至先于阿道夫·希特勒——这个计划的梦想者和构想者;而且他的计划还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我带着我的小册子,”他在一张偷偷从监狱里带出的给苏菲母亲的纸条上可怜巴巴地写道,这也是她们收到的惟一消息,“我带着我的小册子。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从这里出去,见到那些上层人物,让他们看看……”
对死去的人来说,血肉相联形成的爱强烈得令人迷惑,而留在记忆中的童年的记忆也前所未有地鲜明:他与她并肩散步,手指轻轻抚弄着她黄|色的发辫。还有一次,他带她乘上小马车,在夏日鸟语花香的威维尔城堡的花园里穿行。苏菲还记得,当他死亡的消息传来时,她痛苦得万箭穿心。她看见他倒下,倒下——直到最后还在抗议他们抓错了人——倒在萨斯赫森一堵墙前的一阵弹雨里。
第十章 集中营里的幸运者
霍斯住宅的地下室深埋在地下,四周墙壁很厚,是苏菲在集中营住过的可以抵挡焚烧死尸的焦臭味的少有的地方之一。这里也是她的栖身之处。尽管她安放木板床的角落阴暗潮湿,床板下的草垫发出腐臭发霉的味道,在墙壁后的某个地方,从楼上卫生间的小管子里流出的水滴滴嗒嗒地滴个没完,夜里还偶尔会被老鼠的造访惊醒,但总的说来,这个阴暗潮湿的地牢比集中营的棚屋好多了,甚至比六个月前她刚到时与另外十几个在集中营办公室干活的高级女囚住的地方还要好。那里没有集中营最常见的暴行与赤贫,却一直充满噪音,没有一点私人空间。为此她饱受失眠之苦。另外,她也从来不能把自己洗干净。而在现在这个地方,她只和少数几个囚犯共处。地下室提供了一些天使般奢侈的东西,其中之一便是一个盥洗室。苏菲尽情地享用着这一切。实际上她是被要求这样的,因为这栋住宅的女主人,黑德维希·霍斯对污垢有一种病态的憎恶,要求在她屋檐下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保持衣着整洁,并达到卫生要求:洗用水均事先消毒,以致霍斯家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一股杀菌剂的味道。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集中营长官夫人对盛行于集中营的传染病怕得要命。
苏菲在这里发现的另一件好事便是睡觉,或至少是睡觉的可能性。除了食物和隐私,睡眠不足是集中营的一个普遍问题;所有的人都贪婪地寻找睡觉的机会与场所,在受尽折磨之后,睡觉是一种最好的摆脱痛苦的方法。说也奇怪(也许并不怎么奇怪),人们总能做一些愉快的梦。有一次苏菲告诉我,如果刚从生活的噩梦中逃出,又在睡眠中面临另一个噩梦,那些几近疯狂的人们可能会完全发疯。而霍斯的地下室安静,偏僻。几个月来,苏菲总算找到了一个睡觉的地方。她一倒上床便进入梦乡,沉浸在一个接一个起伏的梦潮里。
这个地下室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在木板隔墙的另一边,住着七八个男犯人,大多是在楼上做杂活或在厨房洗碗的波兰人,还有两个是花匠。除非是路过,男女犯人很少碰面。在隔墙的这一边,除了苏菲自己,还有另外几个女犯人与她为伴。其中有两个犹太姐妹,四十岁左右,是从列日来的裁缝。这俩姐妹凭着她们的勤奋和一手好针线活而免遭毒气室的厄运。她们成为霍斯夫人最宠爱的人物,每天和她以及她的三个女儿呆在一起。她们整天不停地剪啊裁啊缝啊,把那些从被送进毒气室的犹太人身上扒下来的衣服重新翻新。她们已在这栋房子住了好几个月,养得肥肥胖胖的,整天固定不变的坐着干活使她们在十分消瘦的同伴里显得异乎寻常的胖。在黑德维希的庇护下,她们似乎不再害怕未来。在苏菲眼里,她们显得十分快活,在二楼那间向阳的房间里飞针走线,把那些印有科衡、罗文斯坦和阿达摩维兹字样的标签从贵重的毛皮大衣和毛料衣服上小心地撕下来,这些东西是几小时前才从棚车上的人们身上剥下来洗干净后送过来的。她们很少说话,但说话时的比利时口音让苏菲觉得怪怪的有些刺耳。
和苏菲同享这个地牢的,还有一个叫洛蒂的患哮喘病的女人,差不多到了中年,是来自柯勃列兹地区的耶和华的见证人。像那两个犹太女裁缝一样,她也是一个幸运者,没有死于“医院”的注射或其他的折磨,而是到了这里,成为霍斯家最小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她有一张梭角突出的脸(下巴向外突出),一双巨大的手,以及平板的身体。她的外表让苏菲联想起从拉文斯布吕斯克派来的女看守——她们中的一个曾在苏菲刚到时对她进行了粗暴的侵犯。不过洛蒂温柔善良,与她的外表极不相符。她像一个大姐姐似的,主动告诉苏菲在这栋房子里应如何行事,还把她观察到的有关司令家和这个家的几件事告诉了她。她让她特别当心那个女管家威尔曼恩。威尔曼恩本身也是一个囚犯,德国人,因犯伪造文件罪而服刑。她住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洛蒂建议苏菲对她说一些奉承话,巴结巴结她,就不会有事儿了。至于霍斯嘛,他也喜欢被人奉承,但不能做得太明显。他可不是谁都能糊弄的傻瓜。
洛蒂是个单纯而虔诚的信徒,几乎是文盲,像一个未经加工的粗陋结实的船一样,忍受着奥斯威辛邪恶的狂风,安详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她没想过要改变苏菲的信仰,只是宣告说,现在她承受的痛苦只能在耶和华的天国里找到回报,而别的人(包括苏菲),都只有下地狱。但她这番话并无恶意。另一次——那天早上和苏菲一起上楼去工作时,她在一楼楼梯的平台处停下喘气,嗅着从比克瑙飘来的焚烧肉体的浓浓焦味,小声咕哝着说了一句“活该”。她说这话时也无多少恶意。毕竟,出卖耶和华的不正是犹太人吗?“罪恶之源,希伯来人。”她气喘吁吁地说道。
我开始叙述的这天,是苏菲在那间屋顶阁楼工作的第十天。苏菲已下定决心要用色相去引诱霍斯。如果不能勾引他(野心勃勃的想法),就求他满足她的愿望和要求。苏菲在洛蒂艰难沉重的呼吸声中惊醒,眼睛眨巴着在地下室阴暗的光线中睁开。透过沉重的眼皮,她看见三英尺外盖着一床被虫蛀得满是洞眼的羊毛毯下的庞大身躯。苏菲本想像往常那样捅一下她的肋骨,但楼上厨房里的脚步声告诉她已是早晨,差不多该是起床干活的时间了。但她想:让她睡吧。于是,像一尾鱼儿愉快地扎进水深之处,苏菲又回到她刚才醒来时的梦境去了。
那是几年前,当她还是小女孩时,与表妹克利斯蒂娜一起来到白云石山。她们用法语小声交谈,寻找着雪绒花,周围全是云雾缭绕的山尖。像所有的梦境一样,她们处在危险的令人困惑的阴影中,但展现在眼前的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