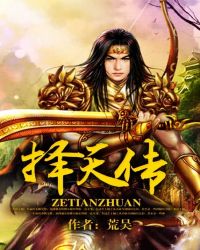苏菲的选择-第7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讲;他神秘地出现在一段历史中,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后,便如同来时一样不可思议地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没有身份,没有形象,只留下一个姓名。他应该被重新发掘出来。那天下午,当我借着酒兴试图向苏菲和内森讲述他的故事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应该将他写出来,把他变成我书中的人物,为世界重塑他的形象。
“太妙了!”我听见自己带着醉意兴奋地大叫,“你知道吗,内森,我现在才明白,我应该用那奴隶的题材写一本书。我们的旅行正是时候。现在这本小说已写得差不多了,可以稍微停一下。我可以做一个全盘计划。因此当我们到南安普顿时,我们可以开车游遍那特·特纳的故乡,和人们交谈,参观所有的古老房屋。我可以感受那里的气氛,做很多笔记,收集资料。这将是我的下一本书,一本关于特纳的书,同时,你,还有苏菲,也可以为自己增加许多有价值的知识。这将成为此次旅行中最奇妙的部分……”
内森用手抱住苏菲使劲搂了一下。“斯汀戈,”他说,“我简直等不及了。十月份,我们就往南方进发。”他瞟了一眼苏菲的脸。他们交换着爱的目光——先是相遇,继而强烈地交织在一起,以至我感到很窘迫,赶紧把目光躲开。“告诉他吗?”他问苏菲。
“为什么不呢?”她回答说,“斯汀戈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不是吗?”
“也是我们最好的人。我们将在十月结婚!”他高兴地说,“所以这次旅行也将是我们的蜜月旅行。”
“上帝,天哪!”我欢叫起来,“恭喜你们!”我大步跨到椅子前,吻了他俩——吻在苏菲的耳旁,那股栀子花的芳香像针似的刺着我的心;吻在内森那高贵的鼻子上。“真是太妙了,”我喃喃地说。我确实是这样想的,早已忘记在刚刚过去的日子里,这样的狂喜往往伴随灾难同时降临。
大约十天或十天后的一天,也就是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我接到了内森的哥哥劳瑞打来的电话。那天早上,当莫里斯·芬克指着过道里那台油腻的付费电话叫我接听时,我大吃一惊——接电话本身已令我吃惊,尤其是这电话是我常听说但从未谋面的一个人打来的。那声音十分温和,可亲,和内森几乎一模一样,带着明显的布鲁克林口音,刚开始时很随便,然后渐渐严肃起来。他问我能否安排一次与他的会面,越快越好。他说最好不要让他到齐墨尔曼的公寓来,而是我到他在森林山的家里去一趟。他又说,我必须知道这事与内森有关,而且很紧急。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于是我们约定在下午晚些时候在他那儿见面。
我在迷宫般的地铁站里完全昏了头,像无头苍蝇似的乱窜一气,结果乘错了车。当我到达时,已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劳瑞十分友好地接待了我。在一片相当阔绰的住宅区里,的站在一套宽大舒适的住宅门前迎接我。还为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一见面就让我着迷。他比内森略矮一些,比内森更敦实,年龄当然也大一些。他俩长得很像,但差别也相当明显:内森神经质,易激动,不可捉摸;劳瑞平和,说话柔声细气,令人宽慰,这可能与他的职业有关,但我觉得更多地来自他那沉稳、刚直的性格。我正想解释迟到的原因,他却很快使我放松下来。他递给我一瓶加拿大裸麦酒,对我说:“内森告诉我说,你是一个麦芽酒的行家。”我们在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前的椅子上落座,可以看见外面掩映在常青藤下的建筑物。而他的话则让我产生如遇旧识之感。
“我想我不必告诉你内森对你评价极高,”劳瑞说,“真的,这也是我请你来这儿的部分原因。事实上,我想你们相识的时间并不长,但我相信,你或许知道他已经把你当成了最好的朋友。他对我讲起你的工作。他认为你是个很不错的作家。有一阵子,你知道——我猜他一定告诉过你——他也曾想过写写自己。只要有适当的环境,内森几乎可以成为任何一种人。我想你一定知道,他有很高的文学鉴赏力。我想你也一定知道,他认为你正在写的小说十分了不起,而且你的南方世界很打动人。”
我点着头,心里充满喜悦。上帝,我多么渴望得到这样的赞誉!但我对这次会面的目的还是摸不着头脑。随后我说了一些话,将对我的天赋与智慧的称赞转移到内森身上。“你对内森的评价很对。你知道,一个搞科学的人居然有这样的文学造诣,更不用说他对文学的价值有如此深刻的理解,这确实令人惊讶。我的意思是说,他既是一个……一个在普费泽这样的大公司里的第一流的生物学家——”
劳瑞轻轻打断我,亲切的微笑中隐藏着一丝痛苦。“请原谅,斯汀戈——我希望我可以这样称呼你——请原谅我,但我必须告诉你,内森并不是一个从事研究的生物学家。他不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他也没有任何学位。所有这一切都是编出来的。我很遗憾,但我想你最好知道这些。”
天哪!难道我命里注定是一个轻信的人,必须与那些糊弄我的人呆在一起吗?我对他们是那样在意。苏菲的谎话已够我受了,可现在,内森——“我不明白,”我说,“你是真的——”
“我是认真的,”劳瑞轻轻插进来说,“我是说,这个生物学家的身份是我弟弟的一个假面具——没别的。噢,他确实每天到普费泽上班。实际上,他在这家公司的图书馆工作,但只是一个挂名闲职,他在那儿可以读大量的书籍而不妨碍任何人。偶尔也帮公司里真正的的科学家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这样可以保护他不受任何伤害。没人知道这一切,包括那位甜蜜的姑娘,苏菲!”
我简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但是他怎么……”我竭力寻找着合适的字眼。
“这家公司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我父亲的朋友。这只是一个很好的帮忙。这很容易安排,内森能控制自己时,他可以胜任规定的工作。正如你所知道的,他毕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甚至是个天才。只是他大多数时候都很不正常,处于混乱失常状态。他完全能做好他想做的任何一件事,写书,搞生物研究,数学,医学,天文学,哲学,等等,什么都行。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他的思想从来没有清楚过。”劳瑞又苦笑一下,默默地把双手合在一起。“事情的真相就是,我的弟弟是一个十足的疯子。”
()
“噢,耶稣!”我咕哝说。
“他患有妄想症,或者说是精神分裂症,我想那些脑科专家也搞不清楚他属于哪一种。但不管怎样,他的确不正常。常常是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他没有一丝发疯的迹象——然后,突然——他失常了。最近几个月他的病情加重了,是因为吸毒引起的。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一件事。”
“噢,上帝。”我又说了一声。
坐在那儿听着劳瑞如此直率而平静地说着这些可悲的事情,我竭力使备受震撼的大脑平静下来。一种近乎悲哀的感情猛然袭来。如果他告诉我说内森患了某种不治之症即将死去,可能我也不会感到如此的震惊与不安。我开始结结巴巴地说,像一个溺水者想拼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可是这太难以置信了。他告诉我有关哈佛——”
“哦,内森从未上过哈佛。他从没进过大学。当然这不是他比别人笨,他读的书比我这一生读的都要多。但如果一个人像内森这样病魔缠身的话,是无法接受正规教育的。他读过的学校有谢泼德·普拉特,迈克林,佩恩·惠特尼等等,是一些非正常人照护院。你刚才说到的是一个收费昂贵的休养农场,他曾是那里的学生。”
“哦,太可怕,太惨了。”我低声地说,“我知道他……”我犹豫了。
“你是说你已经知道他不很稳定,不……正常。”
“是的,”我回答说,“我想傻瓜也能看得出来。但我的确不知道有多么……唔,多么严重。”
“有一次,大约两年前吧,他大约十八九岁的时候,好像完全恢复正常了。但这只是一种假象。我父母那时住在布鲁克林高地一栋很漂亮的房子里,战争还没有结束。一天晚上,在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之后,内森差点把那房子给烧了。那时,我们不得不把他隔离了好长一段时间。那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
劳瑞提起战争,使我想起自认识内森以来一直令我迷惑不解,却总因这样那样原因被我忽略的一件事。显然,内森的年纪正好应该在战争期间应征入伍,但他从未主动提起服役的事,我也把这事儿丢在了一边,心想这是他个人的私事。但现在我不能不问了。“内森在战争期间干什么呢?”
“哦,上帝,他完全不符合征兵条件。在他头脑清楚的那段时间,他确实想参军,但我们坚决阻止了他。他什么也没干,只是呆在家里读普鲁斯特和牛顿的《科学法则》,以及不间断地到精神病院去。”
我很久没有讲话,努力接受这些有关内森的事情。这些情况足以解释一直压抑在我心里没有流露出来的所有疑问与焦虑。我坐在那儿沉思着,一言不发,这时一个模样可爱,大约三十来岁的黑发女人走了进来。她径直走到劳瑞身边,抚着他的肩说:“我要出去一会儿,亲爱的。”我赶紧起身,劳瑞介绍说,这是他妻子咪咪。
“见到你真高兴,”她说,握了握我的手,“我想在内森的事情上你也许能帮帮我们。你知道,我们很关心他。他经常提起你,我觉得他把你当成了弟弟。”
我说了一些附合的话。我还想补充一点别的什么,可她说:“我得走了,你们俩继续谈吧。希望能再见到你。”她真美。我看着她走出去,十分优雅地穿过厚厚的地毯——它在这个温暖好客,豪华但不张扬的屋子里第一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心猛然一动:我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迷人的,知识渊博的,收入丰厚的,拥有一位性感太太的犹太泌尿科医生,而非要当一个贫穷潦倒,苦苦挣扎,作品迟迟不能问世的无名作家呢?
“我不知道内森对你讲了多少有关他自己,以及我们家庭的事。”劳瑞又给我倒了一杯麦芽酒。
“不太多。”我说。确实不多,我一时觉得很惊讶。
“我不想用太多的细节来烦你。不过我的父亲——唔,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从拉脱维亚来这儿时,一个英文字都不会说,但在三十年中,他靠经营犹太人的罐装汤汁发了财。可怜的老头儿,他现在住在护理院——一家很昂贵的护理院。我并不想说得那么庸俗。我把这些告诉你,只是想强调我家完全可以为内森提供他所需要的那种特殊医疗的费用。他得到了最好的治疗,但毫无用处。”
劳瑞停了下来,叹息一声,声音里充满哀伤和忧郁。“所以最近几年里,他一直在佩恩·惠特尼,里格斯,明尼基尔,或别的什么地方进进出出。这一长段日子他一直很平静,表现得和你我一样正常。当我们为他在普费泽的图书馆找工作时,以为他从此可以开始正常的生活了。这在医学上并不是没有先例,事实上,治愈率还相当高。他似乎也很不错,尽管我们得知他到处向别人吹嘘,夸大他的工作,但那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即便他沾沾自喜地编造说新创出了某种神药也无妨。看起来他真正安定下来了,正在朝……唔,朝正常的方向发展,或者说是一个非正常者所能做到的正常。可现在,有了这位甜蜜,悲伤,美丽,让内森乱了方寸的波兰姑娘。可怜的孩子。他告诉我他们要结婚了——斯汀戈,你怎么看?”
“他不能结婚,是吧?他什么时候也像这样来着?”我说。
“几乎没有。”劳瑞停了一下,说,“但怎样才能阻止他呢?如果他又失去了控制,我们可以把他永远隔离起来。那样一切就都解决了。但现在却很难办到。你都看见了,事实上他有很长一段时间表现得很正常。谁会说如此长久的正常不是经过大量医治后治愈的标志?这种的病例报告有很多。难道能仅凭最坏的假设而剥夺他过正常人生活的权利?但假如他娶了那位可爱的姑娘,假如他们有了一个孩子,再假如他真的又一次发疯了,那该多么不公平啊——对每个人来说!”沉默片刻之后,他直愣愣地看着我说,“我不知该怎么办?你有答案吗?”他叹了口气,说:“有时候我想,生活是一个可怕的陷阱。”
我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着,突然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沮丧,像背负着整个宇宙似的心情沉重。我怎么能告诉劳瑞说,我刚刚见过你的弟弟,我亲爱的朋友,处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危险的濒危边缘?我听说过疯狂,但一直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