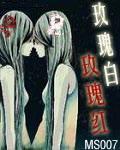大唐万户侯-第17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爱卿免礼!”
李隆基和蔼地笑了笑,他费力地将身子坐正,又道:“适才大堂上朕见你似乎欲言未尽,这里没有旁人,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李清站了起来,整理一下思路方道:“这次改革盐法,最大的人员配置问题陛下已经帮臣解决,地方上又有各重臣去巡查,微臣感激不尽,但还有一件事需要陛下给予明示。”
“什么事?”李隆基的声调忽然拉长,虽然他非常渴望财政能够好转,但李清若事事都靠他,这同样也使他心中不悦。
李清也听出李隆基口气中的不满,但有些话他不得不说。
“陛下,这次盐法改革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皇室宗亲的利益,臣不敢擅自做主,特请陛下明示。”
李隆基沉默了,李清的意思他听得懂,他也知道,皇室宗亲中有不少人都涉嫌倒卖私盐,要想解决好盐政问题,这些人是绕不过去的。
一面是李唐的社稷,一面是李氏宗族的利益,这实在让他难以两全,过了半晌,李隆基仰视着天花板,缓缓道:“朕已经年迈,只盼子女能够平安,李侍郎,我大唐疆域何止万里,你眼光不妨放长远一些。”
李隆基的回答在李清的意料之中,但他也听出了一些端倪,言外之意,除了嫡系亲王,其他宗室他也并不干涉,可任由自己作为,这或许就是他的两全之道吧!
房间里的气氛忽然变得有一点尴尬,沉默了一会儿,李隆基又微微笑道:“朕派七重臣分行天下,监察官吏、推行盐政,你虽为户部右侍郎,但精力主要放在新盐法上,无暇主持户部日常事宜,韦见素还是须留下来,而我大唐的盐产地主要在江淮一带,盐政成败的关键也是在那里,所以朕又考虑了一下,还是由你去扬州比较合适,朕再加封你为江淮转运使兼御史大夫,三日后起程前往扬州。”
李清明白,这是李隆基不想把盐税改革的主战场放在他的眼皮底下,在扬州,即使自己做得过份一些,他也可以装着视而不见,毕竟这次盐税改革关系到大唐的财政能否好转,他李隆基怎么可能不关心。
想到此,李清上前一步,躬身一抱拳,沉声道:“臣,遵旨!”
李隆基暗暗地点了点头,看来李清明白了自己的一番良苦用心,“愿你早传佳报,以慰朕心。”
顿了顿,他的脸色渐渐阴沉下来,身子微微前倾,冷森森的目光盯着李清,压低了声线一字一句道:“你要记住了,朕派你主管盐政并非是因为你草拟此新法,朕是看中了你在西域的冷静、果断,此去扬州,你要拿出点雷霆手段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请陛下放心,臣决不辜负陛下的重托!”
李清告辞,转身便要走,李隆基却忽然又叫住了他,他从御案上找出一本八百里加急快报,对李清笑道:“有件事倒忘记告诉你了,云南刚刚传来消息。”
李清的心一时紧张起来,武行素走了已经有一个多月,却一点消息也没有,着实让他忧心,南诏的局势如何?阿婉现在又怎样,母子可平安?他心情忐忑地望着李隆基,将他的话一字不漏地听进耳去:
“朕采用了你的建议,分几路出兵南诏,扼守各险要关隘,吐蕃人见无机可乘,便退回了神川,凤伽异也随之收兵,但因为国王于诚节战死,他的两个弟弟为争位发生内讧,王:>;除掉了皮逻阁的最后两个儿子,现在南诏居然立了一个女王,听说便是皮逻阁嫁到寒族的小女儿。”
说到此,李隆基斜睨着李清,用疑惑地语气问道:“你在东左右逢源,此女子你应该认识吧!她是怎样一个人?可是偏向我大唐?”。
李清神志恍惚地回到家中,李
话语仿佛还在他耳畔回响,‘南诏居然立了一个女王是皮逻阁嫁到寒族的小女儿。’
他心中仿佛打翻了五味瓶,酸、涩、苦、辣,各种滋味在心中交集,‘阿婉做了南诏女王!’
李清心中蓦地一松,对阿婉应付的责任落下了,可深深的失落感却充斥着他的内心,越来越强烈,痛苦得使他无法自抑,疯狂地吞噬着他的理智,他仿佛行尸走肉般走回自己的卧室,又本能地从床头的箱子里取出一串宝石项链,手颤抖着、轻轻抚摩着这串项链,各种颜色的宝石在他手中熠熠发光,就仿佛阿婉两颗宝石般的双眸。
“李郎、我要取个汉人名字,我要忘记过去。”。
“我如果去找你,我就会跟你一辈子,我不稀罕什么名分,可你也要替我想一想,我也同样渴望做一点事情,求求你,不要逼我,好吗?”。
自己终于失去她了,‘啪嗒!’一颗晶莹的泪珠从他眼角不争气地滑落,李清再也忍不住,忽然扑到床上,用项链狠狠地捶打着被子,咧开嘴、无声地哀哭起来。
“我要去南诏!我要去找她!”他猛地将泪水擦干,摔门冲了出去,这一刻,什么盐政,什么国家兴亡,统统被他抛到脑后,他象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心中只有失去的痛苦,只有一时清高的悔恨。
“老爷!你这是去哪里?”车夫老余眼睁睁地看李清骑着一匹没有鞍的光马,绝尘而去,他吓得连滚带爬,向内院跑去,“夫人!夫人!老爷不对劲了,出事了!。
帘儿焦急地站在大门张望,所有的家人都派出去了,如果再没有消息,她只能去报官,天色昏暗,天际的最后一丝霞红被黑云吞没,夜幕降临了。
就在帘儿刚刚决定要去报官之时,她忽然看见了,长街尽头,一匹疲惫的瘦马驮着一个垂头丧气的人,正一步三拐向这边走来。
“李郎!出什么事了?”帘儿惊惶地迎上去,扶住摇摇欲坠的李侍郎。
“没事,是我发疯了!”李清嘶哑着嗓子,有气无力道。
帘儿推开要扶李清下马的老余,“让我来!”
她小心翼翼地将丈夫搀下马来,又将他的胳膊搭在自己的肩头,将他扶进门去,李清的失态是帘儿首次见到,凭她一颗异常敏感的心,她意识到,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难道是惊雁出事了吗?不会,她中午才从这里回去。’
帘儿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将李清扶回卧房,将他平躺在床上,飞快地给他除去鞋袜,又轻轻拉过被子给他盖上。
‘哗!’地一声,一串宝石项链滑落到地上,帘儿弯腰拾起,她看了看项链,又看了看紧闭双目的李清,缓缓地点了点头,她明白了,是南诏的那个公主出事了。
“李郎,是阿婉出事了吗?”帘坐在床边,轻轻抚摩着丈夫的头。
过了半天,李清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痛苦地思索了很久,他到今天才开始疑惑起来:他当初是不是只有那一条路可走,将阿婉留在东、留在南诏,他现在觉得当初的决定错了,他当时本可以采取另一种行动,在得知阿婉怀孕后,应毫不犹豫地将她带出南诏,带到长安来,或者留在成都,那样也就不会发生今日之事,他的女人、他的孩子都不属于他了,这都是他的错误,他的心已经痛苦得麻木了,被一种强烈的悔恨的感情压倒了。
“帘儿!”李清又叹了口气,他抓住她纤细而温暖的手,仿佛迷路的孩子似的、紧紧不放,“阿婉,她、她现在已经是南诏女王了。”
“什么!”帘儿吓了一跳,“那孩子呢?”
李清摇了摇头,“孩子自然跟母亲,她不来,孩子也来不了!”
“这、这。再刺激李清了。
“帘儿,我觉得很累,心痛得厉害,简直碎裂了一般。”
“累了,你就睡一会儿吧!”
“那你不要走。”李清一把抓住帘儿的手。
帘儿轻轻揉着他的脖子,温柔地在他耳边低语:“你睡吧!我不走,就在你身边,永远、永远。
李清将头紧紧靠着妻子的大腿外侧,感受她手上和身上一阵阵传来的母性的温暖,只有这一刻,他受伤的心才回到了宁静的港湾,渐渐地,他的意识开始模糊,不知不觉,便昏昏地睡着了。
第二百一十二章 求婚
麻麻亮,远空出现一抹紫红色,紫红色仿佛倾翻的酱霭层层尽染,蓦地,披着红火战袍的太阳跳出云端,迸射出万条金线、射透云际,新的一天终于来临了。
李清和往常一样,天不亮便起床,在帘儿的伺候下,洗梳、更衣,吃罢早饭便去了皇城,痛苦化作流汁,漫过层层心田,流去低去,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蓄积起来,成熟的男人会将痛苦放到身后,而将责任放在眼前,他已为人父、为人夫、为人臣、为人主,毕竟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后日他要去扬州了,或数月或半年,眼下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安排,他无暇去细细品味痛苦。
行至户部署衙门口,李清下了马车,正好遇见快步进门的韦见素,二人拱手见礼,李清先笑道:“韦兄,此去扬州,我要抽走数十名户部骨干,让你为难了。”
韦见素上前拍拍李清的后背,感叹道:“本来是我去扬州,或许皇上知道我能力不足,便换成了你,那里牛鬼蛇神众多,各种势力交错,你要当心才是。”
李清听出他话中有话,连忙拉着他进了大门,二人走进内堂,李清急忙问道:“韦兄想必都心知肚明,不妨对李清明言。”
“这。道:“扬州商业极为繁盛,天下一半以上的布帛、油、盐、茶都在那里汇集,京中各势力、各权贵、各利益集团在那里都有势力;相国党、太子党、庆王、永王、寿王也都有心腹、家臣在扬州,所以你虽然身在扬州,但实际上与长安并无区别,阳明,此去扬州,千万不可大意,要谨慎行事。”
“多谢韦兄提醒!”
李清向他深施一礼,又问道:“不知扬州大都督现在是谁担任,还有扬州刺史和长史现在是何人?可有背景?”
韦见素苦笑一声,“这是我最要提醒你之事,扬州大都督由盛王李琦遥领,他常年在京,都督府具体杂事由长史刘汇操持,这可以不用考虑,但扬州刺史是李成式,也是宗室,为庆王心腹,而扬州长史就是李林甫的大女婿张博济。”
‘李林甫的大女婿!’李清摸了摸鼻子,莞尔一笑道:“韦兄为何苦脸,这不是挺有趣之事吗?”
正说着,一小吏跑来急报,“章仇相国来了,请二位侍郎速去相见。”
李清与韦见素对望一眼,异口同声叫道:“快快请相国进来!”
章仇兼琼自入主门下省,在李隆基的默许下,大刀阔斧进行整顿、清肃,他收拢太子党旧人,提拔亲信、故吏,罢黜李林甫势力,仅仅一个月时间,他便牢牢坐稳左相之位,张筠、裴敦复、杨慎矜、李琳、李清、韦见素等大员都愿尊他为首,章仇党的架构隐隐已成。
李清是他的得意门生,现在推行的新盐法也算章仇兼琼推行的改革第一步,眼看李清要去扬州,有些事他必须赶来交代。
章仇兼琼坐下,便急对李清道:“老夫也是刚刚知道你已升为江淮转运使,便急忙赶来,你此去扬州,不仅要推行盐法,还要疏通漕运,皇上既然命你为江淮转运使,自有他的深意,开元十二年,裴耀卿整顿漕运,使江淮之米能大量运到京兆,以至京城斗米不过数钱,开元盛世由此而兴,江南的扬、润、常、苏一带一直便是我大唐最富裕之地,尤胜巴蜀,若能将其物资大量运入京中,便可缓解京城物资匮乏的局面,这就是皇上命你为江淮转运使的深意,你明白了吗?”。
就在章仇兼琼细心叮嘱李清的同一时刻,李林甫也同样在给他的女婿、扬州长史张博济仔细交代。
“李清此子看似年轻,但其手段却颇为老辣,这次杨慎矜倒向章仇兼琼便是他在中间牵线,这次他去扬州,你切不可以貌取人、等闲视之。”
李林甫在章仇党异军突起后,便保持一个低姿态,在新盐法事情上他冷眼旁观,不予干涉,对权术的玩弄,他虽不及李隆基如火纯青,但也是个中高手,审时度势更是他的所长,他位居大唐相国多年,对朝廷的财政危机也深为知晓,从李隆基罢京兆尹、遣七重臣分行天下监督盐法推行来看,李隆基对这次盐法的实施抱了极大的希望,若自己从中作梗,误了大事,恐怕皇上绝不会轻饶自己,但眼睁睁地望着章仇党借这次新盐法之机而壮大,又绝不是他所情愿。
事情似乎有点两难,但李林甫最擅长的权术便是借他人之手,不露声色地除掉异己,李清此去扬州推行盐政,必然会和以庆王为代表的李氏宗室交恶,那他李林甫为何不好好利用一番呢?鹤蚌相争激烈之时、便宜的便是那守侯一旁的渔翁。
张博济年约四十岁,开元年间进士,生得长身挺立、风流潇洒,他文采激扬、为官也颇有几分清誉,为大唐新兴的政治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