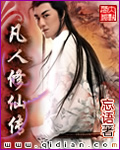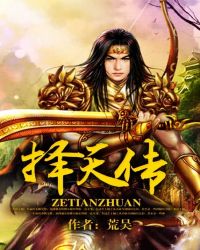韩少功评传-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文学中,企图突破小说形式以获得更大的写作自由度的作家不乏其人,韩少功曾经翻译的米兰?昆德拉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小说中引进了哲学的玄议,插入了词典的小样。对形式的探索有时候是出于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有时候是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让内心的东西能够畅快地流淌出来。
在下乡汨罗的时候,他就发现当地的方言里有许多特殊的词汇,有的发音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时代,有的含义却源自某个村落的典故,因此,外来人要进入当地的语境之后才能听明白其中的所指。不过,他对语词的自觉捕捉是从80年代前期才真正开始。那时候,对湘楚文化的兴趣使他不断寻找机会到湘西去进行田野调查,随身携带的本子不仅记下了一些民歌民谣,也记下了一些别有意思的语词和短句。直到90年代初,参加过海南省作协一些###的人都能够看到,韩少功总带着小本子,有时不知在记些什么。作为作家的韩少功是一个十分勤勉的学习者。就像有的论者所说的,他对语言的兴趣暗合了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存在的本体问题被转换为认识论的问题,认识论的问题又转化为语言的问题,语言成了意义生成和转换的“家”。这种不期而遇的暗合,赋予他语词兴趣以某种现代性,原本是一种文学预备活动的语词玩味变成了具有哲学意义的事情。
大约在1994年年初,一部词典体长篇小说的构思就在他的脑子里渐渐明晰,让他大脑兴奋起来并进入了状态。这一年,朋友圈子里的人就都知道他在鼓捣一本词典小说。为了避免受到干扰,他特地买了一个寻呼机,号码仅告诉少数亲近的朋友,电话则一概不接。他选择自己曾经下放过的、在中国方言版图中最为破碎的地区之一的湖南汨罗,作为小说的基本情景。因为对这里的语言生态、历史文化和生活风貌比较了解,又有过一些记录和思考的积累,小说写得还算顺利,在1995年秋就完成了初稿。
书写得顺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词典的形式巧合了他作为一个知性作家的秉性和散点透视的思维方式。从主体故事结构和主要人物性格的宏大叙事中挣脱出来,小说的结构一下就开放起来,有了许多可以自由进出的口子,作者也从一个接受严格纪律和绝对命令的士兵,变成了一个徜徉在水光山色中览胜的游人,兴起则行,兴尽则止,遇上绝妙的景观即可尽情抒发,否则也可以匆匆走过。在韩少功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随笔中,人们可以留意到他的思维并非遵循单一的逻辑路线,而是带有中国古典绘画中那种普遍使用的散点透视的格局。他没有始终站在一个固定的角度和立场上来观察事物,而是不断地挪动位置,从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立场角度来观照庐山,企图从中获得一种融会于心的贯通,而不是一种定见或成见。这种迷踪的思维给他的批评者带来困惑和困难,于是,他们有时候会把他当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来对待。在散点透视式的观察和叙述中,各个事物都以现象的身份获得平等的地位,它们都可以说是一个中心,并以中心的地位与其他中心交会成为一幅完整的画卷。
在《马桥词典》中,这些分散然而又交融到一起的中心,不是人物和事件,而是一个个语词,它们成为小说的主角,人物和故事只是语词获得意义的因缘聚合,而语词一旦获得意义就有了自己的意志和灵性,反过来改写人和事物的关系。在小说的跋里,韩少功表达了他对语词活生生的感受:“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亡。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笔记本里就捕捉和囚禁了这些词。我反复端详和揣度,审讯和调查,力图像一个侦探,发现隐藏在这些词后面的故事。”作者对语词的感觉,近似于农民对禾苗、庄稼的感觉。因此就有了这本关于语词身世的传奇之书。它的使命可以说是对语词在当代生活中的命运的某种救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马桥事件(2)
表面看来,语词在当代生活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宠幸,用语词编织起来的媒体和书籍堆满了公共图书馆和私人生活场所,使人们越来越依赖它们的逻辑来寻找意义。然而,就像家族专制时代的妃子,一旦在君王那里受宠,就会反身过来干预朝政,语词作为人与人群交流的工具正日益深入地干预着人们的生活,使我们远离原始的经验和感受。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着的今天,为了把更多的人群纳入势力范围,扩大流通领地,语词不断剔出自身特有的原始的感性内涵,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抽象、单薄和乏味。就像都市间呼啸奔驶的公共交通,它们给你带来快捷的方便,但总不能抵达你家的小院。除了有机内涵的减少所导致的空洞化之外,语词的不幸和悲哀还集中表现在它对自己出身的遗忘,就像一个农民的儿子进城之后忘了养育自己的土地和母亲。语词的这种不孝把自己置于无源之水的境地,其内在生命的枯竭也就在所难免。今天,语词听起来都是没有自身生长过程的共时性存在,是从生存经验之外强加或施舍的一种既成的符号系统。《马桥词典》的写作是逆语言发展的历史的一种努力,某种意义上,它是在抗拒汹涌澎湃的普通化进程带来的歼灭性暴力,揭示语词孕育发生和成长的过程,从中来领悟它们被再三剔减的内蕴。而这些被轻易剔出的内蕴包含着的人们对事物至为珍贵的初始领悟。
《马桥词典》展示了语词发生和使用的传奇过程,让我们看到的语词的出生并不是某些词典编纂者和语言学家在暗室里构造杜撰的结果,它们的背后隐蔽着许多生动的脸孔、蹊跷的往事、神秘的意境。它们自然生成的过程是夹带着怒火和泪水、欢悦和忧思、挚爱和仇怨的生活流。每一个词都有人的命运起伏和心灵悸动。回溯语词自然生成的过程,可以帮助人们从语词概念的现成定义退回到尚未构成之前的经验中去,领悟存在难以言说的真实。这也就是从有名返回无名的状态,勘探无中生有的命名过程,其中卷入了种种因缘的聚散。可以说,韩少功所做的工作属于词源学的范畴,《马桥词典》也可以称为《马桥词源》。它通过对马桥地方一个个语词隐秘身世的侦探和解密,了解意义是如何被赋予和剥夺的,以及语言与真实之间复杂有趣的关系。显然,这种努力和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有着承接关系,是一种意义的寻源。寻根更多是寻找一种具有民族气质和风度的表现方式,寻到语言为止,而寻源却是要寻找语言背后的隐蔽的东西,让哑巴说话给聋子听,去解读人性和命运的谜团,拓展悟性的空间。《马桥词典》不乏感性的表达,但它给阅读者更多的是心智的启迪。
《马桥词典》是一部相当人性化的词典,总共收入马桥人生活中的一百一十五个关键词,马桥人生活史上的典故被编入其中,成为词义的注解。通过对众多语词个案的考据,我们发现每一个词都有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于是,一部《马桥词典》看起来就像是一本故事的集锦,而它叙中夹议的写法看起来又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读者不难联想到中国古典的笔记小品。因此,在新颖的着装之下,包含着十分传统的里料。所以作家王蒙这样说:“书里的精彩的故事如此众多如此沁人心脾或感人肺腑,使我感到与其说是韩书舍弃了故事不如说是集锦了故事,亦即把单线条的故事变成了多线条的故事”,“韩书的结构令我想到《儒林外史》。它把许多各自独立却又味道一致的故事编到一起。他的这种小说结构艺术,战略上是藐视传统的——战术上又是重视传统的,因为他的许多词条都写得极富故事性,趣味盎然,富有人间性,烟火气,不回避食色性也,乃至带几分刺激和悬念。他的小说的形式虽然吓人,其实蛮好读的”(《道是词典还小说》,《读书》1997年第1期)。不过,与传统文学中的笔记故事不同,韩少功透过语词来探视不同命运中展开的人性,获得文化上特殊的释义的视角,赋予了故事崭新的寓意,使他不同于蒲松龄等古典故事的叙述者。小说时而叙述时而议论来回穿梭的自由书写方式,也不是小说惯用的熟能生巧的方法。词典中议论为主的篇目看起来像是随笔,叙述为主的篇目读起来像是散文。前者寻求哲思和解悟,后者提供诗意和感动。因此本书也可以称为随笔体长篇小说或散文体长篇小说。虽然怀着知性的使命,但书仍然写得十分轻松,妙趣横生,知性的价值并未与美学的价值相互抵消,同归于尽,而是相互呼应,相互加强。在一些议论性的篇目里,包含着优美的叙述片段;在一些全然记叙的篇目里,也隐含着不用托出的解释。如:《三月三》、《豺猛子》、《红娘子》,它们把概念还原为活生生的经验,似乎不作任何解释,其实是一种最为充分的解释。《红娘子》不仅写出了蛇的阴毒,也写出它的美丽:“山里多蛇,尤其是天热的夜晚,蛇钻出草丛来乘凉,一条条横躺在路上,蠕动着浑身绚丽的图案,向路人投来绿莹莹的目光,信子的弹射和抖动闪烁如花……”但当恶与美结合在一起时,出于恐惧我们往往只看到恶的一面,美也成为恶的伪装或帮凶了。如果不是因为贪生怕死,我们是能够领略和欣赏这种生命身上的华丽的。
()好看的txt电子书
马桥事件(3)
从词义的生成和运用,可以看出马桥人错杂的观念,和他们与自然之间亲切而浪漫的关系。马桥人把我们用于人类和动物身上的“肯”广泛应用于各种事物之中,如“这块田肯长禾”,“这条船肯走些”,“真奇怪,我屋里的柴不肯起火”,等等。这在语法并无错误,但听起来却有些奇怪。这种运用可能是他们对事物的理解与其他地方的人不同,也可能是一种巧妙的比喻,一种诗意的说法。他们把休息表述为“懈”,其实是一种更精准、恰当的说法;而把田埂流水的缺口称为“月口”,则是一种隐喻,源自诗意的联想和优美的情调。“月口处总是有水流冲出的小水坑,沙底,有时候还有小鱼花子逆着水乱窜,提供了收工时人们洗刷什么的方便。女人们如果不愿意去远远的江里,路过这里时总要洗净锄头或镰刀,顺便洗净手脚,洗去脸上的泥点和汗渍,洗出了一张张鲜润的脸以及明亮的眼睛,朝有炊烟的傍晚走去。”(《月口》)
由众多掌故汇聚起来的词典,自然没有中心人物和主体故事结构,这让人想到野生的灌木林,低矮的小树木婆娑地交集在一起,构成了一片葱茏的景色。从细部看,《马桥词典》是一个个短篇故事;从整体看,它却是一部长篇小说。而将这些语词和语词背后的故事关联起来,使它获得长篇小说称号的是马桥这一地缘因素,和许多年前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我”——这个对语词充满好奇和敏感的知识青年。正是这两个因素把人物和事件裹抱起来,使它们不至于分散出去,成为单独的散文随笔篇目。当然,马桥这一地缘只是叙述的起点,而不是边界,韩少功利用“我”与所有孤陋寡闻的马桥人不同的身份,在书中调动了自己在其他地方的生活经验,包括在世界各地不同语系的国家的见闻觉知,来参证自己在这一个小地方的语言发现,通过马桥地方语词与普通话乃至英语等其他语种中相关语词的比较,提供了多种解读生活和文化的可能性,揭示一些被普通话遮蔽的意义,或者补偿语词流失的意涵。
对《马桥词典》的阅读是一个轻松有趣的过程,跟随着那个多年前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知识青年,人们不知不觉就走进了马桥人家,一个个静默的语词也像一只只被惊飞的鸟,舒展起想象力的翅膀,开放出丰富的理解空间。当然,本书仍有一些可以挑剔的地方,尽管作者追求知性与感性的圆融,但词典给予的心智上的启示多于灵府间的感动;众多词条汇聚起来虽然蔚为大观,但词条之间还是显得有些参差不齐,有的词条也只是聊备一格;随着宏大叙事框架结构的解体,作品的沉重感也有所减轻。虽然本义、戴世清、铁香、三耳朵等人物之间演绎出来的故事足够精彩,但对于有传统长篇小说叙事期待的读者,总是不够尽兴。由于缺少对关键性的词条充分极致的阐发来提挈、统摄,作品显得有些松散和芜杂。当然,这些情况恐怕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都与作品本身的形式有关,是作者一开始就必须做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