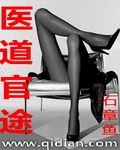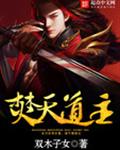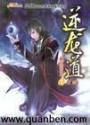君臣道-第4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些贪官污吏相互勾结,企图蒙混过关,大肆行贿。为什么不向岳钟琪和马会伯行贿?因为一向调查官员行贿就等于不打自招,太冒险。
为了查实夔关关税,岳钟琪与马会伯商定,不必查阅以前账目,贪官必定会在账目上做手脚,他们委派原东川知府周彬及马会伯的亲信哈大任为专员,前往夔关监收税银。仅仅80天内,2万两税银已收足。不必监收一年,乔铎、程如丝贪污事实,已是无可抵赖了。岳钟琪与马会伯即将事实奏报皇帝,雍正帝立即命将二人逮捕交由刑部审讯。
刑部侍郎黄炳审得事实,责令程如丝退赔。然而数额太大,程如丝无力退还。问赃银何在?程如丝又交代了重金贿赂蔡珽的事实。
至于乔铎,为何在户部已得到刘天观告发,并据此要求他如实呈报夔关关税时,仍然只报2万两?而布政使佛喜、巡抚法敏,为何首先相信,并为之转呈?户部又是如何批准其所报之数为定额的?于是,一系列贿赂枉法的事实,一一揭露出来。
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刑部侍郎黄炳、川陕总督岳钟琪、四川巡抚马会伯将程如丝贩盐杀人、重贿蔡珽一案,以及乔铎侵蚀税银,程如丝通同隐匿一案,分别定拟上奏。
黄炳等人对程如丝、蔡珽一案,提出了二人俱应拟斩立决的判刑意见;对佛喜提出“负恩悖德”,照大不敬律拟斩立决的判刑意见;对法敏的处理是交部严加治罪;将章孔昭等人拿解到案,追回原得赃银,照例入官;对乔铎从重拟罪归结,而刘师恕也一并交部严加治罪。
据岳钟琪所知,程如丝并没有交待他全部的罪行,黄炳等人却不予深究。岳钟琪又对黄炳等人进行参奏,说他们对一些问题“均未穷追”,事情被雍正帝压了下去。岳钟琪担心他们的罪行既然不能充分曝光,最终可能不会对程蔡二犯实行“斩立决”。果不其然,雍正帝将蔡珽的判决改为“斩监候”,以后又缓期执行,一直拖到雍正帝死去也没有实行,蔡珽最后被乾隆帝赦免出狱。蔡珽竟然不死,这真是“生死有命”,古人称之为“大数”,不知道他命中有何必活之大数?程如丝则在知道被判斩决时就畏罪自杀了,否则也可能不会死,毕竟皇帝当初欣赏过他。
由于岳钟琪没有考虑到雍正帝本人在程如丝和蔡珽的案件中起到的不光彩作用,一味追究,也就开罪了皇帝。后来岳钟琪被满洲贵族大臣们嫉妒,不断受到排挤打击,被撤职削爵,带罪立功,以莫须有的罪名在狱中等死,乾隆帝登基后也赦免了他,并加以起用。
历史上常有这样一种现象: 前朝的宠臣往往不见容于新皇帝,前朝的罪臣却往往被重新信用。因为皇帝总是喜欢使用感恩戴德的官员。对于前朝的宠臣自己不是施恩者,他就可能对自己不忠心。气量狭隘的皇帝就会猜忌他,想办法拿掉他。当然也有两朝元老或三朝元老的现象。前朝的罪臣一旦被重新信用,必然会格外的卖力。这是从权术角度看问题。从道义角度讲,改正过去的错误是新政的首要任务之一。
宠臣李卫
李卫早在康熙年间,雍正帝就知道李卫是一个公正廉明的官吏。李卫在户部任郎中时,有一次,负责收纳钱粮,某亲王要求每收1000两银子就多收10两“库平银”,李卫不同意,亲王强迫他一定要加收。李卫就在户部大堂的东廊下,放了一个柜子,上面写着“某王赢余”,亲王大惊,只好下令停止加收“库平银”。又有一次,某亲王府中的家奴杀人,李卫参与刑部的会审。刑部官员不愿得罪亲王,有意加以袒护,李卫拒理力争,在最终定罪时,同僚们想背着他快速审判结案,会审不通知他,谁知,在会审那一天,他一清早就赶往刑部去了。
雍正帝即位后非常宠信李卫。雍正帝宠信李卫也得力于允祥的极力保荐,允祥一再称赞他“才品具优,可当大任”。雍正帝很欣赏他不畏权贵、勇于任事的精神,称他“为人刚直,忠诚勤敏”。雍正元年,李卫任云南盐驿道,二年升为布政使,三年升为浙江巡抚,四年兼理两浙盐政,五年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六年兼理江苏盗案,七年加兵部尚书衔,复加太子少傅。十年时回京,署理刑部尚书,再授直隶总督。
李卫就任云南盐驿时,雍正帝在总督高其倬的奏折上批示道: “李卫是一出色好员,尔等宜极加爱惜而委用之。”李卫任云南布政使时,有人密参他以气凌人,恃才傲物,粗鲁无礼,受人馈赠。他私下称呼总督高其倬为“老高”,巡抚杨名时为“老杨”,在自己执事牌子上书写“钦用”字样,还接受川马、古董等礼物。雍正帝在批谕中说,对于他的忠诚勤敏是放心的,所顾虑的是: “尔以少年锋锐之气,而兼报效情殷,于上司僚友中,过于强毅用事,致招恃恩犯纵之讥,则又非朕期许之意也。今后须谦能待人,避免以气凌人之咎。”“嗣后极宜谦恭拮己,和平接物。川马、古董之收受,俱当检点。两面‘钦用’牌,不可以已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态,何须乃尔。其克谨克慎,毋忽”。李卫在奏折中表示: “若稍避嫌怨,万难整顿,惟有谨遵礼法,不敢任性,亦不敢委蛇从事。”雍正帝认为他未分清刚直与傲慢的区别,又朱批道: “不避嫌怨与使气凌人,骄慢无礼,判然两途,弗相交涉,汝宜勤修者,惟‘涵养’二字最为切要,务须勉为全人,方不负知遇殊恩,竭力操持可也。”又因人的习性难改,郑重告诫他: “书云‘习与性成’,若不痛自刻责,未易改除。将来必以此受累,后悔何及!”
李卫任浙江巡抚时,多行善政,打击贪官,清查积欠,治理海塘,发展生产,使浙江的经济大为改观。李卫仁慈为怀,济危扶困,赈灾救难,很受老百姓的拥护,其政绩是真实的,比田文镜在盐碱地上收税的做法高明得多。
李卫兼管浙江盐务时,盐枭横行,盐官与私贩勾结,官盐流入私贩。因为官盐奇贵,百姓多食私盐。李卫采取降低官盐价格,控制盐官向私贩走私等办法,整顿食盐市场。大力打击盐枭,使混乱不堪的浙江盐政得以肃清。当时,地方官吏只能缉捕一些中小盐枭,巨商大盗可以逃亡邻省逍遥法外。李卫无法越省稽查盐枭,要求朝廷干预,可是户部不准。由于李卫并非科举出身,又嫉恶如仇,做事不留情面,自然得罪了一些朝中大臣,他在户部供职时想必也得罪了许多户部官员,现在他们就利用职权刁难他。李卫再次呈请,户部仍然不准,李卫坚持所请,事情终于在雍正帝的直接干预下实行了。后来户部在议复李卫关于两浙盐务的题本时,故意称“该盐政”,而不称“该巡抚”,被精明的雍正帝看出有故意蔑视李卫的意思,立即发旨查问,后来将起草文书的司官张复革职,发回云南老家交地方当局看管。
当时江南盗案特多,而江南总督范时绎、巡抚陈时夏柔懦不能戢盗。有一次,陈时夏奏报: 有四人窃得绸布3000余匹。雍正帝批示说: 陈时夏定是受了其下属的蒙骗,岂有四个人能偷运3000匹绸布之理?显然这不是毛贼小窃,而是江洋大盗所为。有鉴于此,他授予李卫总管江南缉盗事宜。为了支持李卫,特设浙江总督一职。
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命李卫兼管江苏缉盗事宜,并参与江苏军政举劾。李卫料到两江总督范时绎将会干扰自己的工作,上奏折说明。雍正帝叫他不必顾虑,“人事参差不齐,何能计较纤细无遗?况且审办公私,最为不易,朕常言,公中有私,私中有公,枢机正在于此。其中原委既不确知,难以批谕”。 所谓公中有私,是就以权谋私而言,无非是求名求利,求名倒也不可一概否定,清官求名与贪官求名绝不相同,李卫不求利而求名,也无可厚非。所谓私中有公,是就人事关系而言,人一旦走入官场,公私就不能截然分开,个人恩怨不可避免要在公事上起作用。要想办好公务,待人接物不可不慎。李卫的缺点是傲气凌人,心量狭窄,容易得罪人,在公事上怎能不受影响?好在雍正帝对他颇为谅解。
李卫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之后,便大力捕盗,连破多起盗案,摧毁多股盗匪。李卫作为封疆大吏不仅仅善于缉盗,而且善于为百姓营造生计,治河修路垦荒,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安定社会之根本。前任浙江总督满保不允许百姓开垦某些荒地,李卫则招民开垦,当年起科收税,余米可运售别地,给票查验,但不许私贩出洋;他贷款给人民修理塘堤;设灶熬盐,官为收买;渔船入海,给牌查验。渔盐收税,充诸公用,既养活了百姓,又养活了官吏,上下兼顾,左右逢源。捕盗与安民,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整治贪官污吏,又增加官员的经济收入,可算是善于行中庸之道了。雍正帝曾在李卫的折子上批示: “汝之一身,即国家经费也,何得看做两事!”雍正十二年,李卫任直隶总督时,有一次与户部尚书海望一同勘查海塘,来到浙江境内。浙江百姓听说李卫到了,以为李卫重来任总督,四方百姓,“蚁屯数十里,欢声应天”,前来迎接,可见其深得人心。
李卫自出仕以来,不瞻情面,勇敢任事,使地方顿然改观,是清朝一位方正大臣,虽然有大毛病,但雍正帝看重的是他忠直的一面。所以尽管他受到多方责难,依然信用不移。
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帝任命李卫为直隶总督。直隶也是多盗之区,李卫严加整肃。当时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违法乱纪,李卫不顾皇帝正宠眷鄂尔泰,依然密奏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扰民。雍正帝览奏十分高兴,他并非在搞权术,要借重李卫来整治鄂尔泰,他是为李卫不畏权臣只忠诚于皇帝的精神而高兴。做皇帝对于臣工“惟知有君”的表现一向都是鼓励和赞赏的。他叫李卫公开上奏章弹劾鄂尔奇,然后命允礼等人审查,但是为了照顾鄂尔泰的面子,只将鄂尔奇革职。人们都知道鄂尔泰是皇帝最亲信的大臣,不敢得罪鄂尔泰。唯独李卫能有如此胆量,皇帝怎么能不激赏他的忠心?雍正帝说: “如果不是深悉朕用人无私的衷曲,怎能毫无瞻顾,毅然直言?”
雍正帝对李卫的骄纵粗狂又谆谆教诫不绝。十一年,在李卫的奏折上朱批道: “何须如此急促,诚可谓躁矣。”十二年,又批道: 有人在朕前说你“任性使气,动辄矢口肆詈……谨言之戒,朕屡经谆训,不啻再三。丈夫立身行己,于此等小节不能操持,尚何进德修业之可期,向后当竭力悛改,时自检点,勤加从容涵养之功,渐融粗猛傲慢之习,则谤毁不弭自消矣。惟口出好兴戎,可不慎诸!”
李卫自辩道: “臣本质愚戆,心直口快,即属官中从无一语轻于肆詈,何况他人!惟嫉恶过严,凡遇公事,即觌面相对,不肯依违曲从。或遇有心钩探藉以进身之人,但能隐而勿答,若问之不已,则于是非二字从未惯粉饰虚词,言不由衷,再加添出枝节,驾辞耸动,结恨益深,此实臣一生招尤取祸之大病。”(《谕旨》李卫)
李卫本是习武之人,识字不多,却注重文事,修方志,建书院,尤其是为浙江士子请命,使皇帝同意浙江恢复科举一事,表明他确实是雍正帝所欣赏的“实心办事”之人。某些人有才华,也能办事,但不实心,雍正帝批评高其倬,总是把保官位放在首位,迎合取悦皇帝,见风使舵,不及李卫朴实无华。雍正帝是很有心机的皇帝,并非昏庸之主。对这种皇帝不可以动心机,他欣赏李卫的坦诚率真。李卫脾气不好,心量狭窄,雍正帝能原谅他,曾对高其倬说“此人但取其心地”,又多次责备他“躁急”,“狂纵”,“骄慢凌人”,“任性使气”等等。如果是换别人,早就将他革职了,哪有如此耐心?他曾赐予李卫御书“公勤廉干”的匾额一方,以表彰李卫的严猛廉洁。
有一次,雍正帝问尹继善,在督抚中谁最值得效法,尹回答: “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也”。
乾隆帝对三人有一段评论: “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田文镜不如李卫,李卫又不及鄂尔泰,而彼时三人素不相合”。
雍正帝所信用的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严刻。在有些人的眼中,雍正帝是一个以阴谋夺得大位的独裁者,他刻薄寡恩,逼死母后,杀害兄弟,屠戮功臣,大兴文字狱,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去。他的继位和暴死都是不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