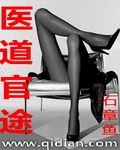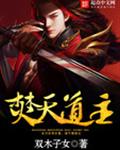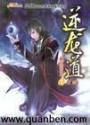君臣道-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下令永停圈地。然而事实上圈占土地的行为,持续了很久才结束。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帝又一次下令禁止圈地。看来,圈地的人不只鳌拜一人,并非只有鳌拜喜欢生夺民间资产,他只不过是一个代表人物。
三大臣抵制鳌拜换田,并不仅仅是八旗内部的财产再分配和权力再分配的斗争,它其实是非正常的掠夺方式与正常的剥削方式之间的斗争,同时也是以乱政治国还是以善政治国的矛盾和斗争。单单依靠暴政不能使清朝的统治合法化,国家政治需要一定程度的程序化。尤其是农耕人口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稳定,能为国家提供一定数量的物资之后,才可以支持这种统治。
剪除鳌拜恢复君权一揽
苏克萨哈一死,朝中无人敢与鳌拜争锋,鳌拜施威震众,益加专横,每奏事则挥臂向前,强说不已,根本不把亲政后的小皇帝放在眼里。康熙帝要使国家政治走上正轨,首先必须摆脱汉献帝似的可悲处境。
鳌拜的妄行,引起朝廷上下普遍不满。有一次侍读熊赐履遵旨条奏时政,暗示鳌拜擅权谋私,要求皇上“朝纲独断”。鳌拜请求治他的“妄言之罪”,并且请求禁止言官上书陈奏,康熙帝不许。康熙帝深感鳌拜“欺君妄为”之恶,决意铲除之。
康熙帝从小由孝庄太皇太后抚养长大,他对这位祖母既崇敬又信赖,每日照例去祖母处请安,听取教诲,每遇重大事件都向祖母请示。太后则充分运用自己的经验才智和威望影响,悉心指导,辅助康熙帝处理军国大事。康熙帝几次向太皇太后提出要剪除鳌拜,太皇太后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告诫他要“戒急用忍”。康熙帝按照太皇太后的吩咐,先加封鳌拜一等公爵太师太傅,施欲擒故纵之计。
康熙帝读书的南书房前面有片开阔场地,孝庄太皇太后为了让康熙帝练习弓箭,特令人在此设立一个箭亭。康熙帝从小就天天在此射兽皮箭靶。太皇太后又定下计策,招集一批身强力壮的满族少年作为侍卫,直接听命于皇帝,由索尼的次子、比康熙帝大两岁的索额图为领队,天天在空地上练武,做布库(摔跤)游戏。鳌拜入宫奏事,常见康熙帝和这些少年跌爬滚打在一起,以为是小孩子玩耍,不以为意。
现在,鳌拜简直不像辅政大臣,倒像一个太上皇,每天与其弟穆里玛、侄子塞本特、儿子纳穆福以及一批党羽在家中议事。国家大事先要经过他们的家庭会议,议定之后,方可施行。他们在朝廷内外,遍布亲信,结党营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些善于拍马的官员,竟把他捧为圣人,比作古代辅佐成王的周公。
周公摄政有“君逸臣劳”的意思,绝非篡权。战国思想家慎到说: “大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主垂拱无为,仰成其事,因此国事无有不治,是治国之正道也。”非常可惜,这种事情,自中国进入成熟的封建帝制以后就很少发生了。像诸葛亮那样的不思篡权的宰相真是绝无仅有。自古以来人们只是消极地强调诸葛亮之“忠”,而忽视了他的以相权治国的巨大进步意义。鳌拜虽然也是以相权治国,但是没有道德可言。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制度不是问题的关键,处在权位上的人才是关键。儒家之所以提倡修身,就是把重点放在人,这是治国的大根大本。
鳌拜见康熙帝现在对自己更加言听计从了,洋洋得意,不可一世。其实,康熙帝正在加紧组织力量,准备行动。他知道,如今鳌拜势力强大,党羽众多,连宫中都有他的耳目,而鳌拜本人亦勇猛过人,许多人都畏他三分。要除掉他,只能智取,不能力敌,还要行动干净利落,不能拖泥带水,以免造成政局不稳。
康熙帝担心训练小侍卫的意图为鳌拜在宫中的耳目察觉,就叫索额图带领小侍卫们练习武艺的同时又斗蛐蛐,又逮麻雀,以此为掩护。索额图见小侍卫们训练得技艺高超,擒拿鳌拜已不成问题,向康熙帝提出可以动手了。康熙帝借向太后请安的机会,向太后请求逮捕鳌拜。为了万无一失,太后让康熙帝在实施行动之前先将鳌拜的一些亲信死党以各种名义逐步派调出京,再擒拿鳌拜本人。
康熙帝遵照太皇太后的主意,与索额图商议之后,分别将鳌拜的胞弟巴哈、亲侄苏尔玛、姻党理藩院侍郎绰克托、工部尚书都统济世等人,先后派往察哈尔、科尔沁、苏尼特及福建等地。为了不使鳌拜生疑,将他的胞弟清西将军穆里玛、儿子纳穆福等仍留着不动。
鳌拜也颇狡猾,有一回假装生病,要康熙帝亲自前往问候,以试探皇上对他的态度。康熙帝亲临其府邸,至寝榻前。鳌拜骤然变色,御前侍卫乃急趋榻前,揭开卧席,见藏有利刃,问他意欲何为。康熙帝神色不变,笑着说: “刀不离身乃满洲故俗,也不奇怪。”其实,他心里有数,鳌拜是心怀不轨,康熙帝马上就离开了那里。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一天,康熙帝召集少年侍卫问: “你们都是朕的股肱耆旧,是畏惧朕?还是畏惧鳌拜?”小侍卫们齐声说: “独畏惧皇上!”康熙帝放心了,然后命人宣鳌拜单独入见,鳌拜昂然而入皇宫内院。康熙帝厉声问道: “鳌拜你可知罪?”鳌拜傲然回答: “臣何罪之有?”康熙帝道: “你欺君擅权,妄杀大臣,罪不胜数,左右快与我拿下!”小侍卫们立时围了上来,鳌拜稍加反抗,便被摔倒在地,痛打一顿,随即将他监禁起来。同时,又将他的党羽一网打尽,都交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处理。
由于事先准备充分,行动起来就干净利落,鳌拜虽然党羽甚多,但一时之间群龙无首,也只能一一俯首就擒。君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何况他们实在不得人心,没有什么真正的力量。康熙帝要将狂妄自大的鳌拜除去,先利用他的狂妄,以退为进,褒奖他,纵容他,使他失去戒心。下手时,康熙帝既不在朝堂上发难,也不动用御林军,而是用这种秘密逮捕的方式来治服他,确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康熙帝看出,用公开的方式恐怕难以奏效,大臣们所以惧怕鳌拜,不仅因为他是辅政大臣,而且因为他是一个大老粗,人们惧怕他本人,因此只要把他治服了,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这种事情往往有一种心理的因素在起巨大的作用。清朝末年,光绪皇帝要夺回权力时,也遇到了这种心理因素的障碍,大臣们早已习惯听命于西太后了,小皇帝即使亲政了,人们也不信服他,他永远是一个傀儡,他要夺回权力必须首先除掉西太后,而这个问题根本无法解决,所以他无可奈何。君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为什么在此时又不起作用了呢?可见,在制度与正统观念这两个因素之外又有另外的力量在起作用。有什么因素呢?是人际关系的因素。这种人际关系的因素似乎是超乎制度之外的。
大臣会议审实鳌拜罪状30条,议将鳌拜革职,立斩,子侄兄弟一并斩首,眷属家产籍没。鳌拜请皇上察看他当年在搭救清太宗皇太极时,身上留下的刀疤箭伤。康熙帝念其历事太宗、世祖两朝,效力多年,屡建战功,不忍加诛,将死罪改为终身拘禁,其子也免了死刑,同党多人处斩,其余分别作撤职、降级处理。数年后,鳌拜在幽所郁郁而亡。
被鳌拜冤杀、革职的大臣都一一平反昭雪。那些依附于鳌拜,不把小皇帝当回事的大臣们,这下可知道了这位小皇帝的厉害。少年康熙在孝庄皇太后的指导下,“戒急用忍”,计除鳌拜,夺回权力。此时,康熙帝只有16岁。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是不好惹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戒急用忍”并非仅仅是一种计谋意义上的小智小慧,它更是一种具有深刻哲理意义的东方智慧,其渊源来自于儒学经典《中庸》。难能可贵的是,在夺回权力之后,康熙帝治国仍然是以“戒急用忍”的态度来开创太平盛世的,而不是好大喜功,任性胡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康熙帝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用“戒急用忍”四字概括,后人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智慧。
从此,康熙帝废除了辅政大臣制,收回了批红之权,所有奏折朱笔谕旨,皆出自他亲手,一直坚持到晚年,他右手患病不能写字,就勉强用左手写,也不叫人代笔。 这些显然都是为了加强君王极权。康熙帝剪除鳌拜集团,独掌权柄之后,深感武人治国的危害,为此大力提倡文治。
第一帝师熊赐履
前文说到,汉族大臣们不可能求得“冢宰”分权的地位,那就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求帝师的地位了。早期儒家都是以周公事业为理想模式的,唐宋时期士大夫还有“致君尧舜”的气象,就是在最昏暗的明朝,还有过一次张居正辅政,都是“冢宰”分权的先例。惟独到了清朝,皇权的旁落除了鳌拜擅权就是太后垂帘听政,都没有积极意义。在清朝初期,汉臣只有做顾问参谋的份儿,士大夫的地位低于满族家奴者,有时甚至连士大夫的尊严都保不住。
康熙初年,参与决策的除四大臣之外,还有议政王大臣、贝勒。这些满洲贵族大多对汉儒文化不以为然,其中孝庄太后的影响力也不小。她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偏爱,自然也是讨厌汉语、汉俗,认为“汉俗盛则胡运衰”,不赞成顺治帝和康熙帝学习儒家文化。但是也有人认为,孝庄太后是喜欢汉学的,康熙帝尊重儒学也是受到她的影响。这就矛盾了,然而历史常常就是这样不明不白的。可以肯定的是,康熙帝从小对汉儒文化就十分感兴趣,首先要归功于他身边的两位原明宫太监,张某和林某。二人原是读书之人,他们不仅教授他四书五经,书写汉字,而且经常给他讲述明朝的宫廷轶事和典章制度,使康熙帝幼年就对儒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幼年教养是何等重要。
儒家文化意识最重视教育兴国,对君主的教育尤其重视。虽然说是“君权天授”,但君德却不能不得之于学养。“天”与“德”也可以画等号,把权力赋予有德之人,是古人“尚贤”观念的体现。心术不正之人,一旦处于至高无上之尊位,必然会给国家带来巨大浩劫和灾难。自然灾难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坏皇帝的祸害深重,所以教育皇帝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大事。封建社会既然不能民选皇帝,就只有通过教育皇帝的途径来“选择”皇帝的贤愚。贤明的皇帝是通过道德教育这一选择方式产生的。其实,皇帝的权力是天赋这一观念的本意,不是指神权与皇权合一,所谓“天择”、“天授”,就是要讲道德,因为道德是源于人之天性(自然之性),人欲则是源于外界刺激。儒家认为,向善是人之天性。今人否认人之初性本善,也就会误解“君权天授”的意思。其实,天就是大公无私之意,“君权天授”就是要求皇帝大公无私。历代皇帝故意歪曲儒家的观念,掺入法家观念,后人就搞不清本意了。
康熙四年(1665年),太常寺少卿钱铤上疏,要求教授小皇帝儒学,他指出: “君德关于治道,儒学尤为急务,请将满汉诸臣中老成耆旧、德行温良、博通经史者,各慎选数员,令其出入侍从,以备朝夕顾问,先将经史中古帝王敬天勤民、用贤纳谏等善政,采集成书,分班值讲,每日讲说数条,不使间断,必能有裨圣德。”这在鳌拜辅政之期当然不可能实行,鳌拜所要的仅仅是权力,而非权力的道德化。权力说到底也就是人际关系,以什么为基础呢?以德为基础,抑或是以利为基础?《左传》说: “君能掌握天命为义,臣能承受天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宣公十五年)所谓“天命”也无非是规律的意思,以义与信谋利,就是符合天命,就是保卫社稷,可以做人民的君主。让皇帝学这些知识,鳌拜是反对的。
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帝亲政,汉族大臣再次纷纷上疏,请求教授皇帝儒学,开设经筵日讲(即为研读经史而设的御前讲席),这些建议仍然没有被辅政大臣们采纳。在他们看来,满洲是从马上得天下,如今以马上治天下,乃是顺理成章,满洲皇帝只需精通骑射,所要学习的也只是“满洲家法”而已。后来康熙帝剪除鳌拜,抛弃清朝“祖宗家法”,“悉承明制”。令人遗憾的是,“祖宗家法”中的积极因素也被抛弃了,“悉承明制”却是把明朝的消极因素加强了。
在封建社会,汉族皇帝或皇太子的教育向来受到特殊的重视。汉朝贾谊说: “天下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