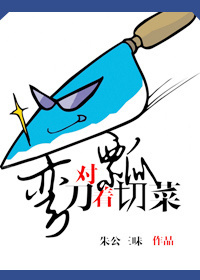曹文轩天瓢-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四部分黑雨(9)
此后许多天,杜元潮一直感到郁闷。尽管房子重新得到修理、篱笆重编织、菜园里的菜得以补栽、屋里被粉刷一新、家中所有被毁家什也一一购置或做了新的,但心里头总觉得发堵,胸口像压了一扇沉重的磨盘。
许多天里,他就一直在暗中追究着那场巨大闹丧的来龙去脉,直到另一件事情的发生:采芹的丈夫死了。
一连下了五六天的雨,那窑工正在窑洞里烧窑,窑洞坍塌了,将他活活闷死在了窑洞里。
这件事情发生在闹丧后的半个月。杜元潮让艾绒去枫桥将采芹带回油麻地,在他家中住几天,但采芹不肯。采芹只是抱着艾绒哭,艾绒见采芹哭,也哭。此后,杜元潮在心中就一直惦记着采芹,总想着见一见采芹,然而又不好去见她,心里很焦灼。
这天,他到县城去开会,散会后没有直接回油麻地,却绕道来到了枫桥。
采芹家的门锁着。
他向人打听采芹去了哪儿,一个妇女告诉他:“刚才看她往那边走了,大概是去她男人坟上了。”
“坟在哪儿?”
“你是她娘家那边的人吧?”那妇女问。
杜元潮点点头:“是。”
“你穿过这片林子,前面就是一片芦苇,她男人的坟就在那边。”
杜元潮谢了那妇女,照那妇女的指点,走进了林子……
初冬的阳光,正照着树林与茫茫的一大片芦苇之间的一条小河,河水安静地闪烁着金灿灿的波光。四周是一个枯萎的世界,到处是败絮、枯枝与落叶。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河边上立着的一座泥土还很湿润的新坟,倒显得有点活气。
采芹弯腰在捡着坟上因昨夜的大风吹折的枯枝和吹落的枯叶。
杜元潮看到了她,没有叫她,而是一声不响地向她走过去。
采芹听见了脚步声,立起身,掉头去看。当她看清是杜元潮时,嘴唇不禁微微颤动起来。
杜元潮在走到离新坟约摸丈把远的地方站住了。
采芹手中的枯枝又重新掉在了坟上。
杜元潮没有去看采芹的脸,却看着别处。他看到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芦苇,看到了初冬时小河中流淌着的漠然的水,看到了在水边觅食的几只褐色的不知名的水鸟,看到了坟,那坟上的泥土是黑色的,甚至显得油汪汪的,看到了坟上的彩色的纸条,那纸条在风中寂寞地飘动着……
低着头的采芹却抬起头来一直看着他。
他似乎感觉到了采芹的目光,就越发地不能将视线转过来看着她,直到听到采芹的啜泣声,才将视线转过来,而这一转,进入他眼帘的采芹竟使他为之一震,心一阵颤抖,目光犹如被击的电石刷地一亮: 清瘦的采芹穿着一身素洁的薄衣,头上扎了一根洁白的布条,更显得头发乌油油的,脸瘦削了许多,有点儿苍白,微带哀伤的眼中似有似无地结着一层薄薄的泪水,双唇有点儿干焦,犹如渴求露水的两瓣花瓣,略显宽大的裤管,欲遮未遮了一双鞋,那双鞋的鞋头上各缀了一小块白布,犹如开放了两朵小小的白花,风从树林与芦苇之间的小河上吹来时,将她胸前两乳之间的衣服向下压住,两只乳房便在衣服下显得更加突出了……
悲哀洗尽了风尘,只剩下冰肌玉骨,瘦劲却又柔弱地在天地间沐浴着清风。
风中,她的身体微微颤抖着。
那略带忧伤的眼神,那苍白与瘦削的面庞,加之这些衣着的陪衬,冷冷的,却又分外的动人。
日后,杜元潮永远都忘不了这天地间百年不遇的新寡之美。他一辈子都会在心中细细品味这人世间可遇不可求的形象。他望着她,目光却越来越没有顾忌。他甚至在心中产生了恶意,血开始升温,并越来越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房。
一对泪眼,她向他走过来,并且一直走到他怀里。
他用双臂一下紧紧地抱住了她。
当她抬起眼睛望着他时,他稍稍犹豫了一下,便立即将自己的嘴唇用力压到了她的双唇上。
她挣扎着,但却将自己的身体更紧地贴向他的胸膛。
他疯狂地吻着她,她的脸颊,她的额头,她的头发,而更多的是她的嘴唇。
她的嘴唇在颤抖,但已变得湿润,并且有了颜色。
他吮吸着她那薄薄的微带凉意的舌头。
她忽然伏在他怀里哭了,并且越哭越厉害,耸起的双肩在他怀中瑟瑟发抖。
他将下颏埋在她的头发里,用双手不停地轻轻扑打着她的后背,眼睛看着那座散发着新泥气味的新坟。看着看着,他的胸膛在膨胀,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他用嘴死死咬住她头上扎着的那根白布条,唾沫不一会儿就将它浸湿了。
她有点儿想从他怀里挣扎出来,但双臂却绕到他的背后,抱住了他。
他突然发疯似的将她向茂密的芦苇丛中拉去。
她抵抗着,但却是绵软无力的。
他不一会儿就将她拉进了芦苇丛,焦干的芦苇发出咔吧咔吧的断折声。
她瘫痪在了地上。
他像一只狼叼着一只小羊羔,揪着她的衣领,将她向这一处芦苇的深处拖去。
由于她的衣服被扯起,她露出了他还在儿时见过的肚脐。
四周是深不见底的寂静。
在将她拖到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那座新坟的地方,他的手松开了。
她有气无力地躺在松软的芦苇叶上。
他一时成了强盗,成了暴君,三下两下就扯掉了她的衣服。她反抗着,而她越反抗,他便越显得歇斯底里。
她用双手捂着双乳。
而就在她的双手从腹部挪移开去护着暴露在阳光下的双乳时,他趁机撕掉了她的裤衩,逼着她将双手从双乳上松开,又再度去护着两腿间那份潮湿的隐秘。
转眼间,她便成了无叶之花。
她终于放弃了挣扎,十分乖巧地躺在了地上。
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欣赏之心,赤裸着身体,粗鲁地进入了她的体内。他听到了她在那一刹那间发出的类似于叹息的呻吟声。他的脑袋正冲着那座新坟。当他在她身体上起伏着时,他透过芦苇看到了那座新坟也在起伏,像一座黑色的浪山。
一个拾柴的小男孩来到了小河边,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从芦苇丛中传来的声音。他想深入芦苇丛去看个究竟,却又不敢,便爬到了小河边的一棵高大的楝树上。眼前的情景使他感到很迷惑:那两个人在干什么呢?他对他们充满了兴趣。他寻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角度,在树杈上坐下来,静静地看着: 阳光下,两瓣白白的屁股在上下颠簸着。
这孩子想笑,但最终没有笑。
在稍微平息一些时,杜元潮发现,躺在那里的采芹,脸看上去有点儿不像采芹的脸,并且显得有点儿小,但却更加迷人。
采芹苍白的脸上,此时早已粉红,并且额头上出来细小而晶莹的汗珠。
有一阵杜元潮的眼睛一直看着采芹头上的那根白布条———那根此时沾了草屑的白布条,使他感到刺激,热血沸腾。
采芹一直泪眼,到了后来,随着浪潮的逼迫,竟然又哭喊了起来,并且泪水愈来愈大。
这哭声与眼泪让那树上的男孩看到的是两瓣白屁股更为猛烈的颠簸。
那男孩终于笑了起来,但却是无声的。
风暴过后的平静,是无人港湾般的平静。
许多天来的郁闷,随之消解,杜元潮躺在采芹的身上,觉得自己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都变得轻盈与空灵起来。
虽然已是初冬,但阳光却是温暖的,且有重重芦苇的遮挡,两人虽然觉得身体有点儿凉,但却谁都愿意那么赤裸着身体躺着。
杜元潮侧过头来时,看到了采芹乳旁的那颗红痣,阳光下,这颗小小的红痣越发的显得晶莹鲜亮,像一粒细小的红宝石镶嵌在白嫩的肌肤上……
第五部分疯雨/胭脂雨(1)
杜元潮一切如常,那场大火所引起的、差一点儿就使他饱尝牢狱之灾的黑风波,似乎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一丝一毫受惊吓的痕迹。他像从前一样,穿着讲究、面容和蔼地出现在油麻地的父老乡亲们面前,没有亢奋,没有疑惑,没有怨恨,仿佛一切都过去了,甚至一切根本未曾发生过。
当邱子东竭力要装出一副很正常的样子来时,他发现杜元潮在看他或在与他谈话时,却比以前还要正常,这反而使他感到了恐慌。他不由得想起当年老同学季国良的那一番话,觉得杜元潮像一口井,被陈年枝叶厚厚实实地覆盖了的老井,深深的,黑黑的,凉丝丝的。但他还是从心里傲慢地抹煞了这点使他痛楚而绝望的感受:见他娘的鬼吧!他依然瞧不起杜元潮,甚至比以前更加地瞧不起。但,他已没有底气将这种瞧不起再公开地流露在脸上了。
常常五更天时,邱子东会被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惊醒。
而杜元潮这里却没有一点儿动静。在油麻地百姓面前,他从不直呼“邱子东”,而总是称“邱镇长”:“这事,你得听听邱镇长的意见。”“邱镇长知道,就行了。”他一如既往,还是不时地让邱子东去参加本应由他这一把手参加的重要会议。会议结束后,他还会亲自主持,由邱子东向班子成员或是生产队干部或是全体油麻地人传达会议精神。
然而,邱子东深刻感受到的,却是一日甚似一日的架空与冷落。
他缺席商讨油麻地重大问题的会议,越来越多。几次他人到了,会已到了尾声。杜元潮看到他,很平常地说一句:“老邱来啦?朱瘸子没通知你今天有会吗?这瘸子,八成是赌钱赌忘了。”接着开会。还未等邱子东的屁股将板凳坐热,会议就宣布结束了。有时杜元潮也会象征性地问一句“老邱你有什么意见吗?”可是未等邱子东说什么,杜元潮还是宣布了会议的结束。会议一结束,杜元潮就往外走,周秃子们也都纷纷走出镇委会,就只有他邱子东孤单而尴尬地坐在那里。坐着坐着,他真想摔凳子砸桌子掀了镇委会的房顶。
每逢这种时候,他就想要戴萍,然而戴萍已经调离油麻地了。有时,他会疲倦地走很远的路,摸到戴萍现在所在的学校,但戴萍是越来越冷淡,越来越没有兴趣了,弄得他很无趣。走在回油麻地的路上,他感到心灰意懒、穷途末路。
这段日子,他迷恋上了打猎。
油麻地四周都是苍苍茫茫的芦苇荡,野鸭、野鸡、野兔、黄鼠狼……猎物不少,因此,油麻地有不少打猎的人。镇东头的胡九,最有名。邱子东找到胡九,说:“将你那支猎枪借我玩几天。”
胡九有点儿不相信:“邱镇长,你要打猎?”
“怎么啦?我就不能打猎了?”
“能打能打,我只是想,一个镇长打猎……”
“不合身份?”
“不不不……”
“胡九,这支猎枪你是不想借了?不借就算了,我跟别人借去!”
“别别别。”胡九立即从墙上取下猎枪,并给了邱子东很多火药,“我哪能不借呀,镇长向我借猎枪是瞧得起我。”
邱子东年少时本就是油麻地的玩主,那猎枪他会耍。
油麻地的人看见邱子东背着一杆猎枪一身猎人打扮出现于田野上时,不免都有点儿吃惊。
邱子东却丝毫也不在乎。
接下来,油麻地的人就会不时地听到一消息:邱镇长打了一只野鸡,有三斤多重;邱镇长打了一只五斤重的野兔;邱镇长埋伏在芦苇丛里,一枪打响,打死了四只野鸭……
邱子东忘记了黑天白日,疯狂地投入了打猎。
邱子东潜行于草丛与庄稼地,出没于树林与芦荡,捕猎的紧张中,有的只是全身心的兴奋与愉悦。压抑不再,恼怒不再,空落落的无聊不再,他陶醉于其中,完全不记得自己是个镇长了。他端着猎枪,躬着腰,脚步轻如猫爪,无声地潜行于麦地里。他像机警的狗一般,站在叶声沙沙的树林里,寻觅四周。为了不惊动水面上一群刚落下的野鸭,他会在五十米开外,就卧倒于地,然后一手抓住猎枪的枪管,用胳膊肘支撑着,匍匐前行,全然不顾地上锐利的芦苇茬将他的衣服与皮肉划破。当他举起被击毙的野鸭时,野鸭血与他胳膊上的血混流到了一起,他会兴奋得在芦苇丛里扯开嗓子大叫,直叫出眼泪来。一只被击中的野鸡带着重伤逃跑了,他见河游河,一路追赶下去,直追得两眼昏花,心血欲要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