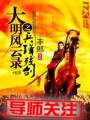晚清风云-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原来师丹里已退休在家,上野和他熟稔,见面后先介绍清国的正副公使郭大人和刘大人,师丹里立刻笑盈盈地上来与客人握手,并将客人引入宽敞豪华的大厅,主宾落座后,上野代表郭嵩焘说起来意:感谢师丹里爵爷在报上撰写同情亚洲人的文章。
师丹里不由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他的个人所见,认为英国人在大清有四件事做得极不光彩:第一是不该倾销鸦片;第二是不该拥有领事裁判权;第三是传教士不遵守法度;第四是马嘉理一案错在英国,不该反赖大清赔偿并开放口岸。
其实,英国人用坚船利炮叩开大清的大门后,硬是五凶十恶,又岂止这四端呢?但郭嵩焘和刘锡鸿听了仍如醍醐灌顶般快意,口中连连称善,并和师丹里谈了打算,师丹里认为找外交部交涉是对的,并口口声声保证,有机会一定要代为游说国会。
修改条约
回到使馆,郭嵩焘等人对改约一事更有了信心,想到第一步——国内交办的两件交涉案尚无回信,正准备派人去催问,不想就在此时,邮差送来当日报纸,《泰晤士报》第四版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报道了“禁止鸦片协会”开会并上书国会的消息,其中有清国公使的即席发言一节,另外却在左上角用醒目的字体发了一条消息,谓清国公使自己即是一个鸦片吸食者,每日在使馆吞云吐雾、一榻横陈云云。
使馆之人听凤仪念出后不由大哗,郭嵩焘更是气得绕室徘徊——平日认《泰晤士报》立论公允,不偏不倚且常发表同情大清的文章,不料今日竟如此黑白颠倒、信口雌黄,洋人的反复无常,与市井小儿何异?
这中间刘锡鸿表现尤为激烈,他立刻把马格里找来,将报纸往他面前一扔说:
马清臣,你们英国人怎么血口喷人呢?”
马格里不知刘锡鸿气从何来,也不明白大厅里的人为何个个对他竖眉瞪眼,像审案一般,乃捡起报纸仔细浏览一遍,终于看到那篇文章,不由淡淡地一笑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黎庶昌说:“我们使馆上下无不洁身自好,才到此地便约法五章,其中之一便是禁食鸦片烟。这是你所看到且也应该遵守的,正使大人对鸦片更是深恶痛绝,这也是你天天看到的,可报纸居然如此颠倒黑白,这可不是一般的污人清白,而是别有用心呢!”
于是众人纷纷质问,就像文章是马格里写的一般,马格里无奈,只好说:
“大家还是少安毋躁的好。”
刘锡鸿说:“这是何等大事,叫人能不气愤?”
马格里说:“我们大英帝国一向讲究言论自由,凡各有所见,均可在报上撰文发表,就如你们朝廷的御史可风闻奏事一般,不必件件落在实处的。尤其是在竞选的时候,为诋毁对方,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你若认真,那可会气死呢。”
张德彝也闻讯赶来,代为宽解说:“这《泰晤士报》原名《每日天下纪闻》,创刊约在乾隆初年,属汤姆森报业集团,所载文章均是自由撰稿,并不代表政府。我看可能是正使主张禁烟的话触怒了一些鸦片贩子,于是他们便造作出这等谣言来。”
经他如此一解释,众人认为合理。但这事不但关系今后修约之议,且事涉正使脸面,甚至是一国之名誉,岂能小看?大家议来议去,决定紧急约见威妥玛,先看他有何话说。
“啊呀呀,就为了这件事?”
威妥玛风风火火地赶来,大概在路上已听黎庶昌说了,进门便用十分轻松的口吻说:“小事一桩,去一封信让他们更正并向郭大人道歉就是。”
郭嵩焘听他说得如此轻松不由更加有气,乃说:“如此信口乱喷,假如是发生在你们身上,不知当作何处置?”
当作何表示,威妥玛其实心中有数——自从《烟台条约》签订后,国内外反映不一,因条约规定鸦片在中国的销售必须税厘并征,大大地伤害了东印度公司鸦片贩子的利益,故他们对此群起而攻之,加之俄法诸国也对英国单独与中国的商定不满,故有不少人从中作梗,今日报上发表此文,决非无因。不过此时此刻,他怎么好对郭嵩焘说呢?只好笑了笑,说:
“也不过一笑了之。”
自从得知英国国会迟迟未能批准《烟台条约》后,郭嵩焘早已明白其中底蕴了,眼下他见威妥玛期期艾艾,知他的难言之隐,但此事牵涉到个人名誉,他终不能释怀,乃说:
“这里才说本人在夏弗斯百里家发表禁烟的演说,那里又说本人吸食鸦片烟,如此反复无常,那我成了什么人了?”
威妥玛被他问得无言可答,只好说:“报纸纯一家之言,并不代表政府立场,若硬有侵犯名誉之事,可以请律师和他打官司,不过,据我国法律,像这类事也无法科以大罪,无非是道歉了事。但不打官司国人或许知之不多,一旦打起官司,反弄得举国皆知。不如依我所说,倒可得息事宁人之美名。”
郭嵩焘尚在沉吟,威妥玛又连连好言劝解,并说自己将亲自去报馆交涉,保证更正与道歉的文章第二天同时见报,郭嵩焘才稍消其怒。
威妥玛走后,马格里又反复劝解,据他说泰西的言论自由,确有为东方人所不能理解者。他说了一件往事:一日女王与一班文学侍从之臣在宫中举行宴会,席上有人提议即席编故事,要求是一要简短,以一句话为宜,二要关于女王,三要牵涉到风流韵事。各人临场发挥,都有作品,最后选定的一篇众人皆说好,你说这篇是如何写的?原来他竟写道:
“女王身怀有孕,谁干的?”
你想想,谁都知道女王与丈夫感情甚笃,居孀十余年仍为丈夫服丧,怎么会有这等事呢?当时大家都捏了一把汗,可女王听了也不过一笑了之。
眼下众人听马格里说起,一个个都觉得匪夷所思。在中国,普通人就是确有其事,别人也不敢说,又何况事涉宫幄内秘呢?
郭嵩焘却始终轻松不起来——此事不管怎么说,都有些蹊跷。因为一面是他发表关于禁烟的演说,一面却诬蔑他本人吸鸦片烟,而且,绘影绘声,什么“一榻横陈”、“吞云吐雾”,哪有如此巧合呢?
第二天上午不到送报的时候,威妥玛便带个随员来了,手持一张尚散发油墨香的《泰晤士报》,见人便扬了扬。郭嵩焘闻讯迎出来,在台阶前与威妥玛相遇,威妥玛得意洋洋地说:
“郭大人,这下放心了吧?”
郭嵩焘让张德彝把更正的文章口译与他听,张德彝念道:
“昨日本报记者琼斯所写谓大清国公使吸食鸦片一文,采自传言,与事实不符。大清公使郭大人立身端正,从无不良嗜好,为一体面君子。本报特予以更正,并向郭公使道歉,且保证今后不再发表此类文章,望郭公使宽大为怀,不咎既往云云”。
文章措词还算得体,郭嵩焘及闻讯下楼的刘锡鸿等人听了,这才脸上露出了笑容。台阶上不是说话处,郭嵩焘乃伸手肃客,把威妥玛和随员让进客厅,又让佣人摆上水果点心,且端上咖啡,接下来谈第二件事——昨天是气头上不想说,今日正好接续前言:
湖口的盐船案、镇江的趸船移泊案,照会到外交部已一个星期了,何以不见回复?
到得此时,威妥玛的面色立刻凝重起来,头一偏,口气颇为倨傲地说:
“这两件事发生时,本人尚在贵国,首尾都十分清楚,简言之,不就是死了一个水手么?你们的照会也才到5天,急什么呢?”
“死了一个水手”仅指湖口的盐船案;而镇江的趸船移泊关系江堤可能坍塌,危及垸内数十万人的生命,却避而不提,再说“死一个水手”就是小事么?“马嘉理案”也才死一个翻译呢,可你威妥玛却掀起翻天浊浪,百般恫吓,险些就发动一场战争。
想到这里,郭嵩焘把心里想的委委婉婉地说了出来,并说:“我们的照会虽只发了几天,可案子已拖了两年了。”
威妥玛正在喝咖啡,闻言放下杯子说:“要说两年也事出有因——此案敝国派在上海的领事麦华佗博士本已作了了断,可你们原告不服才拖下来。眼下交涉到了外交部,外相慎之又慎,要派大员专办,这就必先调集案卷,派员复核。须知我们是法制国家,听讼时为免出偏差,手续十分繁复,怎么能在近日就能答复呢?”
其实这也就是答复。可发生在大清的事,为什么大清的官员不能根据大清的法律作出裁决,而要交由洋人审理,官司拖了两年,又从上海转到伦敦来,何以舍近求远呢?话说到这份上,自然归结到中英间的不平等条约之一的领事裁判权了。
郭嵩焘想把话说得委婉些——在这件事上,威妥玛是关键人物,他是现任驻华公使,有关大清的事,外相以他的意见为主。
正想缓缓进言,不想刘锡鸿先发言了。
这些日子,刘锡鸿也研究了不少外交文件及国际法准则,故开口也有理有据。他说:“这事归根结底错在领事裁判权上,根据国际公法,外交豁免权是正当的,领事裁判权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你们的传教士、商人在我国犯了法,我们官员不能管呢?所以,我认为,要想两国永远相安,应该重新考虑修改中英条约。”
话未说完,威妥玛立刻站了起来,手一挥,打断了刘锡鸿的话。
自从日本公使提出修改不平等的条约后,外相德尔庇已料定清国公使必然效尤。尽管英国与欧美各国的条约都无领事裁判权这一条,他们也料定清国公使已掌握了有关情况,但仍一脚踩定条约不能修改。威妥玛已接受外相这一训令,故当刘锡鸿才开口马上堵他道:
“郭大人、刘大人,你们今天究竟是为了两件具体的案子提出商讨,还是要公开指责我们的前任政府呢?如果要撕毁前任政府已定的条约,那正好,才签订的《烟台条约》墨迹未干,我们的国会尚未批准呢。”
一见威妥玛突然变脸,郭嵩焘认为刘锡鸿出言太陡,忙用和缓的语气说:
“不要急,威大人还是坐下来吧,都是老朋友了,见面何必激动?我们算是朋友之间的谈心吧。”
威妥玛见郭嵩焘态度从容,相比之下,自己却是急躁了些,于是坐下来,但仍用咄咄逼人的口吻说:
“谈什么?谈你们不想履行条约?”
郭嵩焘说:“此话从何谈起?要毁约我们何必来?须知本公使来到贵国就是为了履行条约的。不过,中英之间历次所订条约确有不完善之处,应该斟酌、修改,刚才刘大人的意思便在这里。”
威妥玛一听,鹰眼直逼郭嵩焘,连连追问道:“斟酌?修改?条约就是为了约束双方行为而签订的,订者,定也,怎么还可修改?反复无常、信口雌黄怎么能取信于人呢?”
郭嵩焘望他冷冷地一瞥说:“阁下不必把话说得太绝了。其实,中英之间自第一个非正式条约——《穿鼻草约》起到眼下的《烟台条约》止,其间屡有更改,《南京条约》就是在《穿鼻草约》的基础上有所增加,《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又是在《南京条约》上层层加码,只不过每修改一次,更加有利于贵国,敝国则更加不堪罢了。再说,条约每十年修改一次本是列国的规矩,也不是我们兴起的。”
威妥玛经郭嵩焘一反驳自知失言,但仍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说:“本人认为英中之间所有的条约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而订,十分合理,且经两国元首盖印,经敝国国会批准,毋庸再议。”
熟悉中国朝章典故的威妥玛此番终于用了一个“毋庸再议”了,但郭嵩焘从他话语中看出了心虚和强词夺理。事情既经刘锡鸿点明了,他决心率性说下去,于是说:
“不然,这以前敝国尚未开放,在事大臣不谙外交,也不知一些外交原则,故不该答应的事也答应了,就如领事裁判权,据本人所知,这是针对野蛮国家而设立的,并不针对文明国家。我中国为五千年文明古国,当今皇上、太后为一代仁厚之主,内修法治,外睦友邦,贵国视我大清为野蛮国家,乃是不友好的行为。”
郭嵩焘原想这一番话入情入理,应可折服威妥玛,不想威妥玛竟连连冷笑道:
“既然阁下有此一说,本人不妨把话挑明。不错,领事裁判权确是针对野蛮国家而设,因为敝国法令乃根据耶稣基督的教义——要拯救有罪之人的灵魂而不是惩罚肉体而设。故一向宽大人道,敝国人民也习惯在这种宽松法律下生活。贵国自诩文明法治,据本人所知,法治极不